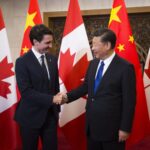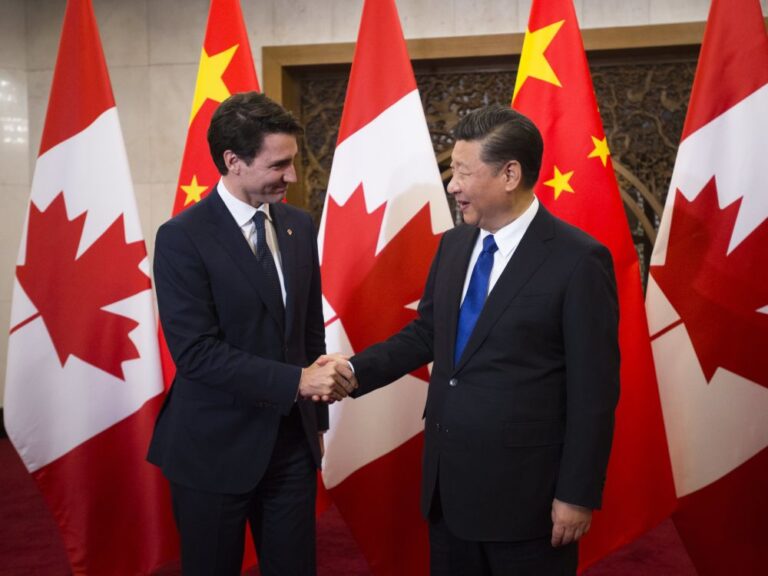图片源于:https://www.vulture.com/article/a-canadian-coming-of-age-gem-is-now-available-in-the-u-s.html
照片:纪念碑发行
一个在PT巡洋舰中烧录的Sum 41专辑光盘。
VHS录像带复卷器上盖子的咔嗒声。
一部DVD封面恐怖到让你在Blockbuster旁边走过时本能回避目光。
我们曾拥有可以握在手中和拥有的实体媒体,或至少可以租借的媒体。
在每个购物中心的街区,我们都曾有视频商店。
我们曾是一个正经的国家,而在黑色幽默的《我喜欢电影》中,这个国家便是加拿大。
在她的首部影片中,编剧兼导演陈德尔·勒瓦克怀念并再现了她在2000年代早期的多伦多地区青少年生活,甚至还刻画了一个假视频商店。
来自于电影和音乐新闻行业的她,讲述了青少年电影迷劳伦斯·克维勒(Isaiah Lehtinen)的故事,劳伦斯像是《高保真》中的杰克·布莱克,但他是一个拥有库布里克迷恋症的情感受困少年。
最终结果是一部关于成长的珍品,专为Letterboxd的爱好者量身打造,让你想紧紧抱住自己的DVD,思考当初自己对妈妈多么糟糕的态度。
在2022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首播后,勒瓦克自嘲称之为“红药丸版本的《法贝尔曼》”,现在终于可以在美国购买或租借。
勒瓦克与Vulture一起,边喝蛋奶酒边聊到了打破“枫树天花板”的经历,以及她为何将这部电影视为对未来厌女粉丝的早期干预。
这部电影关于一个小孩,他需要电影就像需要呼吸一样,这显然是非常私人的情感。
作为青少年时,你与流行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
我作为青少年时对流行文化的印象是如此强烈。
我觉得我通过自己消费的电视节目和电影活着。
当《洞房花烛夜》中的乔伊与佩西第一次接吻时,我体验到的兴奋和欢愉超越了我自己经历的任何一次接吻。
作为一个在郊区孤独的书呆子,模拟出流行文化符号在我灵魂的构成中产生了强烈的交织。
我与斯特劳斯的第一张专辑以及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作品有着原始的关系。
我想制作一部反映我的青少年经历的青少年电影,那就是在停车场等妈妈来接的青春时光。
电影的主人公并没有去舞会,也没有任何现实的爱情故事,他只是需要面对自己的自恋与特权。
那正是我高中最后一年的经历。
我记得我对纽约文化的沉迷也非常强烈,因此我会在走廊里做一些奇怪的显现练习,假装自己身处我从未去过的东村。
我觉得很多青少年都有这种感觉,没人像我一样理解这一切。
而我认为这在一个16岁男孩身上比在我16岁时的自己身上显得更可爱。
由女性导演制作的关于男孩的成长故事是非常罕见的,你为什么想讲这个故事?
在电影的早期阶段,我会见了一位女性电影制作人征求建议。
她问道:“为什么是一个男孩的故事?这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它是一个女性角色,你更容易获得加拿大艺术资助。”
但我认为改变主角的性别让我能够以更自传和真实的方式讲故事,因为作为一名电影制作者能够有更大的距离。
而且,针对女性导演的《法贝尔曼》比较会无限延续,甚至可能会对电影造成影响。
因为我从18岁起就是一名流行文化评论家,我的整个职业发展和艺术审美都围绕着男性,无论是我的导师还是我约会过的男人,甚至是我试图取悦的对象。
我对他们感到有些同情。
他们都是如此扭曲和破碎,似乎不知道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运作,或如何将女性视为人。
我认为这都是因为他们也消费了那些有毒男性艺术品。
我想知道他们在高中时期是什么样子,于是产生了某种早期干预的想法,或者说帮助他们走上修复的道路,以确保他们不会成为非常糟糕的电影评论家,或者像达伦·阿伦诺夫斯基那样,穿着七条围巾。
我对他们充满同情,因为他们以各种方式影响了我的人生:渴望成为他们,渴望他们爱我、肯定我和给我认可。
可是然后某个时刻你会意识到,他们曾经都是这些在视频商店里哭泣的16岁小孩,观看《爱在心里口难开》的那种。
这个角色对我来说非常有趣,可以深入挖掘。
照片:纪念碑发行
劳伦斯与他视频商店老板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引人入胜的动态。
这个16岁的小男孩对自己非凡的未来充满信心,而这个30岁的女人必须处理他的棘手处境,并且他们之间以某种方式是彼此的镜像,互相施加创伤。
我感觉这正是女性在文化中被灌输的:让位于劳伦斯们,尤其如果你在艺术界是女性。
我认为很多女性的工作就是思考男人的想法和感受。
在我和朋友们的对话中,我们总是试图给男性更多内心的思考,甚至比他们自己可能拥有的还要多,来为他们的行为辩护。
所以对我来说,女性应该非常善于写作男性角色,因为我们不断地在分析男性的行为。
在代表性方面,女性讲述男性故事的这些空白给了我们一种不同的视角,看到的男性角度也许是他们自己看不到的。
我成长过程中消费过许多由男性制作的成长电影。
我因为想去看《园中小屋》而跳过了我的新生周。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在想,为什么那对我如此重要?
为什么没有一部女性版的《园中小屋》存在?
电影开场是“拒绝之夜”,这是劳伦斯和他的朋友马特·马卡尔丘克一起制作的视频。
你是如何掌握那种2000年代早期业余视频的美学和喜剧风格的?
我爸爸找到了我在高中时拍摄电影时使用的迷你电视摄像机,然后发现了所有那些旧录像带。
我在高中期间和朋友们一起制作了许多电影,看到我当时做的那些糟糕影片真是太惊人了。
与我在高中时制作的相比,“拒绝之夜”简直可以说是一部典藏级作品,但其中有一种喜悦和极其书呆的纯粹性。
因此,我们致力于追求那种iMovie 3的美学,并且还参考了孤独岛的风格。
其中也融入了许多加拿大文化。
当Swollen Members同意将他们的歌曲授权给我们时,我真的哭了。
说到哭泣,这部电影非常搞笑,但在严肃的时刻却又让人心碎。
你是如何确定这种基调的?
我感觉劳伦斯在写剧本,而我只是他的秘书,进行记录。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他的声音对我来说立刻就很清晰。
我记得写下一个场景时,听到他的声音说:“这就是因为我爸爸自杀的原因。”我当时想:“什么?!”
这令我感到震惊,即便是对我自己来说。
我对此人经历过一些创伤的想法很感兴趣,同时认为这并不代表他们的行为就可以得到原谅,并且指出你仍然需要为你的行为负责。
这又是另一个令人伤感的小男孩的典型情节:他们就是不会为自己的行为年复一年承担责任,并继续施加类似的伤害。
这部电影并没有宽恕劳伦斯,或者像我认为如果由他来导演的话那样抬高他。
在当了超过十年的艺术记者之后你如何决定转向制作电影?
在我心里一直有这种想法,自从我在高中时拍摄那些可怕的电影开始。
我有这个渴望,但我不想给它命名。
我在多伦多大学上过电影学校,但我的教育甚至是如此严谨和学术,以至于让我不敢认为我能拍电影。
我只是想着我不是戈达尔,或简·坎皮恩。
我非常害怕甚至尝试。
但做评论的工作是一个安全的方式,与我想做的工作相邻。
我热爱电影评论。
我发现了保琳·凯尔和韦斯利·莫里斯。
我也喜欢查克·克劳斯特曼,他是我1990年代的另一个英雄。
我20岁时住在纽约,曾在Spin实习,在评论唱片时体验到了一种奇怪的、非常搞笑的千禧年名人效应。
你的CD评论被打印出来,贴在唱片店的CD旁边,你觉得:“好吧,我在奉献些什么。”
但在某种程度上那是一个微弱的声音,直到它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呐喊。
在很多女性感到生理钟在滴答作响,需要生孩子的时候,我感到我需要拍一部电影。
于是我需要搞清楚,谁会让我怀孕?
照片:凯特·基莱特
你必须把劳伦斯生孩子。
我美丽的儿子!
寻找这个出色孩子的Casting过程是怎样的?
这段过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就是这部电影的精髓。
他出现在每一个画面中。
他从不停下喋喋不休。
你需要一个有魅力、可爱、迷人到能够让观众原谅他愚蠢行为的人,但同时他也必须是一个有 considerable 较大边缘和动荡感的劣势怪人。
如果他是一个非常好看且正常的人,这部电影将行不通,整部电影就会崩溃。
我们对于许多青少年和年轻成人电影中期望的可爱、温柔、白板式观众替代品只是由一部分人组成。
我需要一个实际上有相当的边缘和波动性的人。
因此我们进行了范围广泛的加拿大全国Casting搜索。
来自《法贝尔曼》的加布里埃尔·拉贝尔也来试镜了。
萨米·法贝尔曼!另一个年轻的电影迷!
我的剪辑师看过后,她说:“哦,我的天啊,陈德尔!这里有一个惊慌失措的场景!这里有一个学年年末视频!”
这两部电影同时上映,一些人在TIFF做了双排放映。
我认为你得先看这部电影。
或者某种程度上,这适合当成法贝尔曼的调剂剂。它更短!
但最终是以赛亚赢得了这个角色。
我观看了100个试镜带,看着30岁和12岁的人假装成为劳伦斯,实在是太奇怪了。
以赛亚是最后一个试镜的人之一。
他的录像带并不是我所期待的,但却要更有趣和复杂。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真诚,而那个信念是如此强烈。
我记得我妈妈看过他的录像带,那是他在餐桌上朝母亲大喊的那一幕。
她说:“他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他有星星般的魅力。
但他太像你了,人们会不喜欢这个。”
我当时就想,我觉得他刚刚获得了角色。
当你第一次拍摄一部如此私人的电影时,演员与导演之间的合作非常重要,他们必须真正觉得自己是电影的作者。
我正在寻找的就是那类电影和演出:艾尔西·费舍尔在《八年级》,杰森·施瓦兹曼在《拉什莫尔》。那是那些演员的电影。
你给他布置了作业吗?
是的,他看的是所有他未曾见过的电影,因为他主要喜欢动漫。
所以他看了《鬼城》和《拉什莫尔》,我还让他看了《弗朗西斯·哈》。
他表示这样让他害怕成为成年人。
我们一起看了《怪物史莱克》和《史莱克的圣诞特辑》。
这一切都是在疫情中通过Zoom进行的,所以我们第一次在拍摄前两周见面,但到那时我们已聊了好几个小时。
罗米娜·杜戈在电影中饰演阿拉娜,同样出色。
她是另外一个自我录像带,我之前并不熟悉她的工作。
她参加了《加拿大发现之舞》的第一季。
我觉得因为她是舞者,她的身体语言十分引人注目。
而且我喜欢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感觉。
照片:汤姆·伍德
在将这部电影推向世界并看到人们反应后,你的感受是怎样的?
在大部分制作过程中我和我爸爸在伯灵顿一起居住。
我当时回到了怀旧的状态,正翻看高中时的物品,甚至穿上了我的旧运动服。
然后在完成电影拍摄的三周后,我摔断了腿。
因此在石膏和拐杖的状态下我在家剪辑整部电影。
我父母曾经观看过电影的片段,因为我总是在观看编辑,或者我爸爸会路过我在与剪辑师在Zoom中的画面。
第一次完整观看时,我爸爸告诉我:“我以为会很糟糕,因为就是这个小男孩在尖叫。
但还有其他场景!”
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经历,制作如此私人、带有我自己的音调和真实声音的作品。
我之前拍摄的短片和音乐视频更像是自我的延伸。
我之前写过个人随笔和评论,但那仍然不等同于创造一件艺术作品。
在你希望影响的那类电影发放时,如何面对那些电影男人?
我可以为任何哭泣的男士提供拥抱,以换取他们的克里特丽DVD。
如此难得的是,加拿大电影获得了如此多的关注与热爱,但《我喜欢电影》在纽约票房火爆。
你能谈谈自己如何制作出这部非常加拿大式的电影吗?
这是通过一个叫做“人才培养”的资助项目制作的,这是加拿大电台(Telefilm)的首部电影资助。
当时我从中获得了125,000加元的资助(约91,000美元)。
你无需偿还;没有附带条件。
他们甚至不会给出建议或影响演员选择。
与美国的体系相比,那里每个人必须完全自筹资金或找随机的富人给予资助,拥有这样的艺术资助简直令人欣喜。
接着我又获得了加拿大艺术委员会的资助。
所以这完全是基于各种资助。
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持,我根本就无法制作这部电影,甚至没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同时,我们的体系完全基于政府给艺术家拨款,这其中显得有些奇怪。
什么才是加拿大艺术,如果政府在决定什么是有价值的?
这种施加存在出于何道理?
我知道人们总是对英语版的加拿大电影抱有偏见,认为它们低劣,或者具有一种难言的虚假感,仿佛是某个美国电影的模拟。
我不太看到很多加拿大电影旨在成为大众的喜爱。
甚至连加拿大人都很少知道一部加拿大电影的存在,因为没有宣传它们。
这些电影大多注定失败。
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想,我会成为那部不失败的加拿大电影。
而我仍然无法获得美国发行资格。
这是一种破裂的格局,充满了许多障碍。
感觉就像是你撞上了“枫树天花板”。
这部电影如此具有特定的加拿大化特征。
此外,这部电影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安大略省伯灵顿的景象首次展现在观众眼前。
铭记你成长的地方是重要的。
每个人对自己的出生地都存在爱与恨的关系。
我们驾车环游伯灵顿,拍摄那些死去的购物中心和停车场,使用的是潘avision相机,这对于我来说意义深远。
作为一个总是被怀旧感困扰的人,我觉得自己只是在拍电影,以理解我生活中的奇怪片段,并向前走。
我想这些电影只是我自己的一种沉浸式疗法,所以现在我对青少年时光的反思更加坦然。
你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我希望能在今夏拍摄我的第二部电影。
[作者注:这次访谈发生在今年早些时候。]
我在蒙特利尔拍摄。
这是我的独立摇滚电影。
背景设定在2011年,关于我在蒙特利尔独立摇滚场景的经历。
它讲述了一个年轻的女性音乐评论家搬到蒙特利尔,为阿拉尼斯·莫里塞特的《烦恼的源头》撰写一本33 ⅓的书,之后她沉迷于一个很糟糕的乐队男孩。
这个项目由马特·约翰逊和马特·米勒制作,他们参与了《黑莓》的创作。
我已经与我青春期的时光和解,而下一部将讲述我二十岁出头的故事。